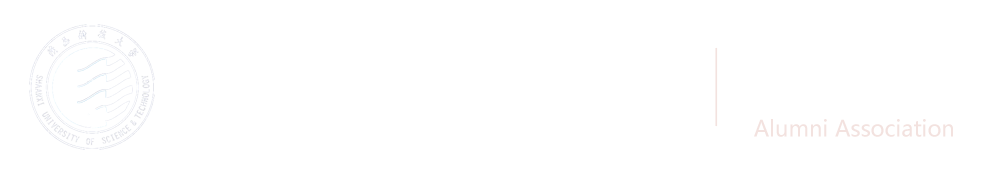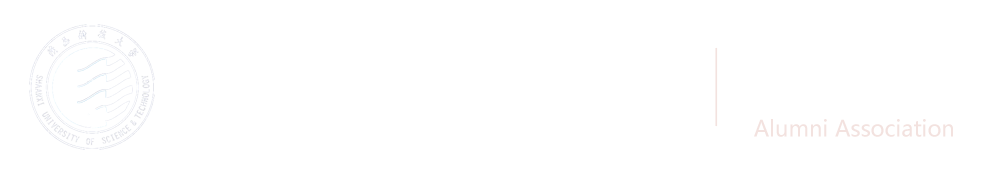1968年12月26日,我坐火车离开了北京,前往唐山,踏上我生活之旅的新征程。
这一天就正是毛主席75岁生日,北京满大街上都是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庆祝的人群。喜庆的氛围它分散了我当时离开北京与亲人分别时暂短的惆怅!
我在唐山地委报了到,就住在其招待所,吃在其大食堂。我第一次吃黑乎乎泛紫色的白薯面的窝头,喝淡黄色玉米面稀糊糊。几天的饭食,我知道了这里供应不同北京,粗粮多细粮少。这也预示我离开北京今后生活习性将从新开始。要适应当地习惯,做吃苦耐劳的准备。
以前我没到过唐山,她一无所知。据旁人介绍说,唐山是河北省重要的一个工业城市,有许多工矿企业。陶瓷厂产品也很有名气。
多光听别人介绍了,还想实地了解一下实况。有一天,我和几个待分配的大学生们,直接走进了唐山第一陶瓷厂。说明来意,厂方热情接待我们,介绍了厂里现实情况。到中午还管了我们几个人一顿午饭。我是学硅酸盐专业的,陶瓷厂该算是对口的单位,厂方也愿意接受。但听到说这个厂的“文革”两派还较劲,我不知道应站在哪一方,我婉言谢绝了。因为我在招待所里,就曾见到几个已经分配下去的大学生返了回来。说是因为所到的接收单位分两派联合掌权,非要他们表态是站在哪一派。他们刚到不了解情况,不好表态就被退了回来。我担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我在唐山地委招待所住了三天,了解唐山、等待分配。每天就是绕街。进入眼球的是:各个煤矿附近“黑雾”随风飞扬;而水泥厂周围 “白尘”铺天盖地;钢铁公司高炉“黄烟”滚滚喷出。唐山市区的空气,给我不好的印象。
从负责分配的同志那里,通知我们的分配有两个去向:唐山市、秦皇岛市。
报道限期临近了,我决定去秦皇岛闯闯,尽管那里我也一无所知。
12月30日,我取得了到秦皇岛组织部报道的介绍信,登上去秦皇岛的火车。
一下火车,只见车站就是几间平房,一间较大的平房里面生着火炉,就是候车室兼售票处。拎着行李出站,我找公交汽车站,想打听怎么走去报到处。看了四周一圈,发现火车站竟没有一路公交车。秦皇岛市让我惊讶!
此时天已是傍晚,我只能一边走一边向路人打听,好不容易找到文化路市委组织部。工作人员已下班,门卫指路,我来到招待所先安排住下了。第二天上班,再去组织部出示介绍信报道,当即分配我到秦皇岛耐火材料厂。拿到‘派遣证’,我又徒步寻路耐火厂。
1968年12月31日。我按期到厂报了到。明天就是69年元旦,厂子放假,又是先安排我暂住在厂子的招待所里。所谓招待所就是厂办公楼里的一层,预留的两个有床铺空房间。
晚上倒在床上,回想来的一路,在这个城市里,我没见到一幢像样的楼房和商厦;所走的路大多是土路。矮矮的平房,窄窄的街道。街上行人、车辆也很少。秦皇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好‘土’哇! 这儿虽称作市,比起我去过的城市真太小了。不过直觉告诉我,这儿的空气的确比唐山要好上许多。
住招待所这几天,有人对我介绍说:秦皇岛耐火材料厂隶属冶金部,生产钢铁厂用的耐火砖,算是秦皇岛较大的企业。耐火材料也属硅酸盐专业门类,和我所学专业基本对口。心想在学校学了那么多年专业知识,在这儿应该发挥一下知识的力量。报效祖国一直是我的初衷。
元月6日工厂上班,我被安排在粘土砖车间当工人。车间主任直接领我下到车间。
我身着工作服,带好大口罩,走进车间。只见在灰暗的光线下,有十几台摩擦压砖机在运转,发出吭哧,吭哧有节奏的响声。多数机器上由两个人操作:一个是开机器的司机,另一个人负责装料,取出压好的砖坯。大家头都不抬,马不停蹄地忙碌着。车间里粉尘飞扬,空气十分污浊。人们都带着大口罩,只露出双眼,分不清男女。
在一台个儿最大的机器前停下,指着一名他们管他叫“科长”的工人,这是我的赵师傅,跟着他干。(以后知道赵师傅叫赵国玉,他是共产党员、班组长。但为什么叫他“科长”,后来才明白,原来他说话有些“嗑巴”)。
我的任务看起来很简单:就是往压砖机的钢模具里装入压砖使用的土料,砖坯压好再搬出来。连续重复操作。装多少料是要经过秤称量的。压出的砖坯也要检查其尺寸是否合格。这台机器压的砖坯叫‘十枚’(它一块重相当十块标准转),一块砖就净重72斤之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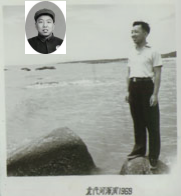
人生地不熟我很少说话,按师傅要求,只是埋头干活。第一个班八小时下来,班长说我们压了260块砖。每一块都是用我的双手(俩人抬)捧出的呀,算算有18720斤之多。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干这么重的体力劳动。
晚上我躺在招待所床上,浑身酸痛,好像连吃饭的劲都没有了。我知道,知识分子是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,刚一上来就这么“照顾”我,我必须抗住!……。
我安定了工作后,就搬到职工单身宿舍住。宿舍就在这座楼三楼,六个人住一间。每人一张木板支撑的床。我带来的盛衣物的木箱就塞在床下,肥皂、牙具放在窗台上。毛巾都搭在贯穿室内的一根铁丝上。洗衣服到公厕洗漱池,晾衣服、晒被子就到楼顶平台上。
就这样,每天上班下班,一个月下来我吃掉45斤定量口粮(在当时这是干重体力劳动人的定量),但我的体重也降到我参加工作后的最低点。从保留下的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到那消瘦的脸庞。和我大学毕业时的照片相比判若两人。轻工业学院毕业的我,如今跳进重工业行业,完全逆反了我个人的心愿,我的身板能行吗?我当时真的怀疑自己能否扛得住。
头半年,一切都很陌生。我每天就是上班、吃饭、睡觉;在车间、食堂、宿舍三点循环。我很不习惯的就是这里工人的三班倒。
星期日休息我就是洗洗衣服,没有亲朋可访。厂子距离商业街市区较远,没有汽车,往返路途都要步行1个小时之多。所以很少上街。我来这一年后,秦皇岛终于有了①路公共汽车,可是因为车少,等的时间长。于是出现一句顺口溜:“秦皇岛有一怪,坐车没有走着快”。北京看惯了车水马龙,乍到这儿单从感官上就不适应。
当我拿到第一份工资42.5元时,我感叹终于自己能养活自己了。我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,省吃俭用。一年后,我靠自己攒的120元钱,在北京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。
在秦皇岛我没有同学、亲朋,生活单调,我很想请假回北京过年。但厂子不给我假。直到大年廿九,这天下了夜班(凌晨1点),我就直奔火车站,大年三十清晨返回北京的家。和父母兄弟高兴度过上班后第一年春节。三天节假过完我返回秦皇岛,没耽误一小时上班。
那时候从秦皇岛到北京,坐火车途径天津要六、七个小时。票价才7元6角。
可能领导是要锻炼我,在耐火厂两年多,我的岗位换过多次。从粉碎配料,到压砖成型、干燥,再到烧窑、开窑,成品检验。整个生产流程我全干过了。
在粉碎配料班 大块的熟料堆在料场,先经人工选料剔除铁器杂质,然后工人装上手推车,喂给‘鳄式破碎机’初级破碎。一个人一辆带斗的铁皮手推车,再装700—800斤的孰料,各干各的。我长那么大没推过车,一个班下来对一个身高不足1.6米,体重不过百斤我该是多大的困难!那时候,耐火厂不管你是新来的,年轻或年老的,每个工人都这样。重体力劳动,每个人都很累,没人能帮你!初级破碎后由皮带机送至‘轮碾机’再次压碎,然后送到‘球磨机’细加工,磨出的熟料粉,比白面还细,稍一动就飞扬起来。我在这里工作,粉尘弥漫整个操作间,干活就是戴上口罩也不及于事,鼻孔内还是黑黑的。
在机压成型车间 摩擦压砖机不停地转,秤量,装料,压砖,出坯。一天我刚下班回到宿舍,便听到车间出事了,小宋(加德)的右手被压断了。出事的机器就是我干活的机器。回想起我们当班时,老师傅察觉机器有问题,就提醒大家小心。事故和我擦肩而过。老工人的经验很管用,受伤害的常常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。
在烘干半成品车间 是个封闭的房间,脚下是热炕,上面码着待干燥的砖坯。一个班8小时在里面,完全是人工翻坯、捣垛,无数次弯腰再直起的重复。闷热、潮湿一直陪伴着你,不见阳光,工作服始终被汗水浸润而又不能脱下来。
在烧窑班 厂区有六座露天的‘倒烟窑’,有很大的露天储煤场。烧窑者要自己去煤场用小推车将煤运到窑炉前。冬天煤场的散煤冻成一坨,需用尖镐刨开。‘倒烟窑’烧窑是要人工用铁锹往炉门内加煤的。胸前炉火烤,后背冷风吹。夏天,头顶一草帽,面对炉火烤。即使大雨滂沱,也必须用坚持。因为窑一开烧,中途就不能停火。烧窑需有经验老师父才能胜任。因为把握不好火候,一窑的砖坯就会全报废。前面的所有工作将前功尽弃!在这儿我只管从煤场往倒烟窑前运煤,或清理炉灰。
在装、开窑班 那时厂里用的是“倒烟窑”。烘干的砖坯搬进窑,码满窑室,称‘装窑’。取出烧好的成品叫‘开窑’,都是靠工人进出窑炉,双手操作,纯体力劳动。为了争取时间夺得高产,不等温度降低,工人们穿着工作服、头上披着打湿的麻袋片,脚穿厚底鞋,双手垫着厚厚的手垫,冲进到窑内出砖。每人坚持不了三分钟,就得退出来换人。因为窑内温度太高,时间长了衣服就要烤焦了。装窑是技术活,如何把砖坯码入窑内,使其均匀受热完成烧结是关键。这里劳动强度最大,主要是工作条件高温,干活似是与时间赛跑。
我在这里只能参加开窑,把成品耐火砖装在排子车上拉出窑炉,身上被砖头粘的滚烫的石英沙粒烫出小水泡是常事。
在成品库 在露天场地上,堆放着一垛垛才出窑的耐火砖,等待验收是否合格。检验员每一块砖,都要经过双手量尺寸是否合格,双眼要看砖的成色,有无铁斑。双耳要倾听声音,判断有无裂缝、夹层。同时还要再一块砖一块砖地重新码好垛。检验合格后,再经过人工草绳打包避免磕损,才能出厂。一个班一个检验员,需弯腰千万次才能完成任务。不能拖拉,因为有买货主人在场监督,并催着要清点发货。这里的劳苦我自有体会。
实践中,我深深体会到工人劳动强度之大,老工人师傅个个腰痛。一年之内我自己也得了‘腰肌劳损’和‘坐骨神经痛’。上班必须坚持,下班就去医院治疗。春节休假期间我回京,在宣武医院求医,通过拍片,得知我还有隐形椎裂。
秦皇岛耐火材料厂设备陈旧也落后,安全没保证。在我到厂两年半内,竟有三个年轻工人的右手被压砖机器压断。整个厂区粉尘弥漫,有不少老工人患了职业病——矽肺,呼吸困难痛苦难言。
上大学时,我们曾参观过北京耐火厂,那里厂容洁净,车间不见粉尘。工人都是站立操作摩擦机,文明生产,秩序井然。看到这里的境况,我私下查找了许多相关资料,对照自己学过的知识,曾筹划过关于‘安全生产和防尘改革’个人的建议。
但当时文革极左之风在厂里依然时兴。技术人员靠边站,知识分子被称为“臭老九”。‘造反派’当家,就知道高呼“抓革命”口号,“促生产”就是一味追求完成产量指标。自誉“大老粗”的车间负责人,人们称他们“小耳朵”、“张大嘴”。根本不信任知识分子,厂里原有的技术员都搞边站了,他们一人说了算。
举例说吧:有一天班后学习时间,我主动向领导提议,我负责给每天大家读读报纸。我知道干活论技术、体力我比不上工人师傅,可毕竟我不是文盲,是北京人,普通话读报还能胜任的。 但得到头头的回答是:你不能!你现在是在接受“再教育”! 俨然是把我划入另类!?言外之意:知识分子——甭想别的,你只有干活,接受劳动改造!
给大家读读报,难道这是非分之想吗?!我不怕艰苦,尽管我的体力较弱,但我一直坚持我的工作量,不比旁人少。但是像这种歧视,使我困惑、失望和不悦。心底里感到有些凉意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曾经设想好的改革建议只能‘死于腹内’。
工人师傅对我还不错,知道在我秦皇岛只身一人,没有亲朋。他们思想上帮助我,找我谈心;生活上关心我,帮我缝衣、做被。还曾主动给我介绍女朋友。那时秦皇岛市场物资供应还不充足,我每次回京也帮师傅们,代买这里奇缺的衣服物品,以示报答。
1970年元旦我是在厂子过的,人生地不熟真没意思。但第二天晚上发生的事,我记忆深刻:
晚上都十点多了,没啥干的,宿舍里大家都躺下睡了。一阵紧急集合号声把人惊醒。
“起床,起床!山海关编车站失火了,基干民兵全体集合去灭火!”。
我是基干民兵,毫不犹豫起身下楼集合。我们坐着厂里的大卡车飞驰而去,我心里想火场会什么样,这回救火大家可要表现勇敢点,争取立功。
一路上车很多。 山海关我也没去过,黑夜中也不知道车到了那儿。车走了大概半小时多,车忽然速减了,停车了。前面传来大火已被扑灭了。我们的心立刻放松下来,这时才感到天很冷。来的时候着急,穿的都不多。还有的没穿袜子,没戴帽子。在急速行驶的敞篷卡车上冷风飕飕。回到厂才发现耳朵冻出了大水泡。第一次我以工人的名义参与,也表达出工人同志在关键时刻的大无畏的忘我精神。
1969年3月,边境发生了珍宝岛战事。中苏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。1970年的年底,毛主席提出“深挖洞,广积粮,不称霸,备战、备荒为人民”。全市范围大搞挖防空洞,组织全民防空演习。耐火厂自然不例外,下了班,我们还要去挖防空洞,修渔轮码头,八小时之外作贡献。
1971年元月,秦皇岛市还组织野营“拉练”。我参加了这次野营“拉练”。当时我是指定连部文书。我的工作就是,汇总连队所属各排拉练每天情况;写稿件表彰好人好事:写感谢信,搞好与驻地村民关系,当好毛泽东思想宣传员。
“拉练”生活主要就是走。每天早上7-8点种出发,下午4 -5点到宿营地。几百号人大队伍浩浩荡荡,步行在田间大路或曲折蜿蜒的山梁上。行进中不时还进行防空袭演习。
集合、出发,休息、防空演练,全营的一切行动都听从司号员的军号声。到了营地(村庄)以班为单位领取做饭的粮食、柴禾(专有打前站的后勤同志与村里联系好),自己生火做饭。晚上还要站岗巡查。纪律:不准私自行动,不准买零食。野营拉练当时我们的口号是:走一点红一线,住一处红一片。提高战备观念,加强工农联盟,巩固无产阶级专政。
拉练开始大家心情非常好,边走边还有歌声。一天下来不少人脚底上打起了泡泡。几天下来脚上打泡的多了。此时身体好的主动帮弱的拿东西。同志们相互鼓励,坚持步行“拉练”不掉队。
自元月4日—21日,17天的野营拉练,进抚宁、跨卢龙、越昌黎,徒步涉过三个县两个区,翻山越岭行程580余里。
拉练整个行程,我一直坚持步行,认真完成文书的工作,也积极做好事。“拉练”最后一站——昌黎,在进行的总结会上我被大家评为先进个人。
在耐火厂我干了近两年半,这是我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第一站。他磨练了我的意志,增强了我的自信心。过去总以为自己这不行,那也不如人家。现在我相信自己,只要是我想干、爱干,坚持干下去,事情一定都能作好,因为,事在人为,有志者自有千方百计!
作者简介


白凤余 男
1943年出生 原籍 北京市 中国民进会员 中学高级教师。
1957---1663年 就读北京师大附中
1963—1968年,北京轻工业学院硅632班学习。
1968年毕业,分配到秦皇岛耐火厂工人。
1971年组织调动到北戴河中学,任物理教师。
1985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秦皇岛市委员会。
1998年抽调到北戴河区教育局教研室,中学物理教研员。
2003年退休。从教32年。
我的电子邮箱;bdhbfy@163.com